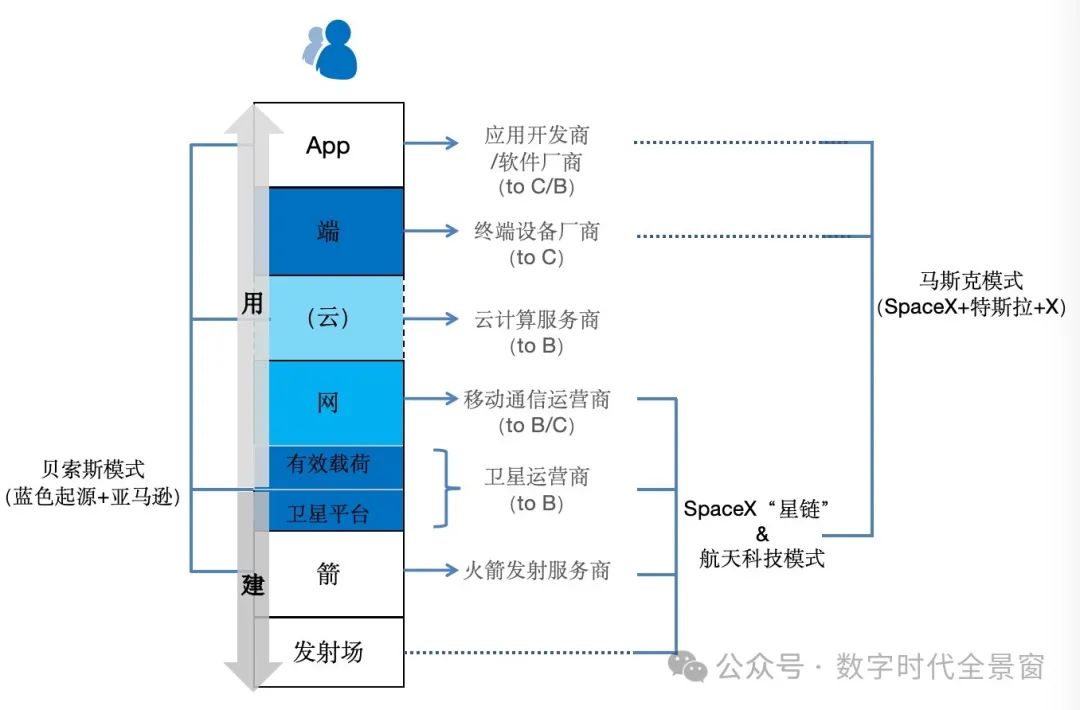
一旦客户在地面站接收到卫星数据,就可以立即在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Amazon EC2)实例中处理它,将其存储在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S3)中,应用AWS分析和机器学习服务获得洞察力,并使用亚马逊的网络移动数据到其它区域和处理设施。





1 月 13 日 23 时 25 分,长征八号甲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试验十八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实现火箭院 2026 年发射开门红。

长八甲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18组卫星,实现火箭院2026年开门红;遥感五十号01星成功发射,用于国土普查与防灾减灾。同日商业航天板块深度回调,两只概念股因信披问题收监管警示。

葡萄牙成为第 60 个签署《阿尔忒弥斯协议》的国家,承诺践行深空负责任探索原则,愿为和平利用太空贡献力量。